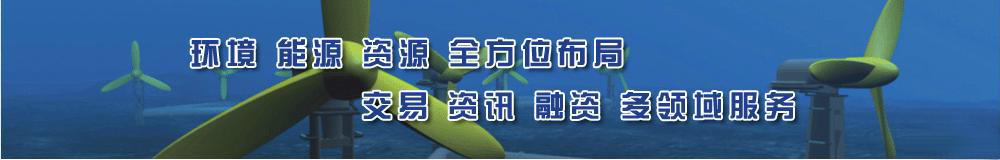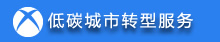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G20杭州峰会前夕,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点燃了舆论关注“绿色金融”的热情。随后在G20杭州峰会上,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主持的G20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向G20峰会提交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正式发布,在全球财经政策层面和金融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第五届“生态文明·阿拉善对话”上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围绕《指导意见》所提出的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政策激励措施、第三方评估和评级以及上市公司环境披露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我国支持绿色金融系统性属国际先例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绿色投资理念还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广,金融机构还高度依赖政府的政策“信号”,因此与市场自然发展的模式相比,政府牵头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可以大大加速其成长。
证券时报记者: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您觉得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马骏:我觉得,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七部委《指导意见》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系统性。《指导意见》囊括了所有的主要金融工具和相关部委的政策工具来动员和激励绿色投融资,这种系统性属于国际先例。在欧美国家,一些绿色金融工具发展得比较早,但多数是靠市场主体自发地从单个金融工具和自愿性倡议进行推动。比如一些金融机构发起自愿性的赤道原则来推广绿色信贷、一些金融机构发行了绿色债券、英国建立了绿色投资银行、美国发明了Yieldco、几个开发银行开展了绿色项目担保、一些保险公司开发了绿色保险产品等。但是,除中国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政府层面来推动各类绿色金融工具的全面发展,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系统地整合了各类激励机制。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绿色投资理念还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广,金融机构还高度依赖政府的政策“信号”,因此与市场自然发展的模式相比,政府牵头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可以大大加速其成长。比如,去年底我国监管机构和政府支持的机构出台了绿色债券的指引和界定标准,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在此后半年之内就发展成全球最大的规模。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此前的解读文章中,提到此次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出现了多个第一、首次。《指导意见》中,最让您个人振奋的是哪些内容?
马骏:一个是设立国家级绿色发展基金,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绿色产业的信号作用。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为绿色项目提供股权融资的渠道,防止出现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绿色项目要获得银行贷款或发债,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以股权投资为主的绿色投资基金可以补充绿色项目资本金。另外,绿色发展基金在一些绿色产业可以树立样板和标准。因为很多绿色产业涉及到新的技术,新的应用,所以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出面支持新的绿色项目可以在标准设定方面为整个业界提供基础。
另外,再贷款也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为我国首创。过去再贷款用于一些结构调整的项目,比如小微、三农,已经执行了很多年。国家希望金融业在补短板、支持薄弱环节方面发挥作用。其实绿色产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板,现在生态这么脆弱,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这么严重,就是与环境保护的投入和服务不足有关,所以这个短板也需要靠绿色金融来补。
证券时报记者:关于建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此前,您在多个场合提过,推进绿色金融,政府资金仅能发挥撬动民间资本的作用。对于这一举措应该如何解读?
马骏: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不足。绿色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国家财力又非常有限,因此就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每一块钱的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放大。
国际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英国绿色投资银行,成立于2012年,是一个国家级的绿色投资机构。最初由英国财政部投入30亿英镑,资本金回报率达到9.9%。据了解,他们一块钱的政府投资能够撬动三块钱到四块钱的民间资本。这就说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够比较好地结合起来,同时能够撬动更多民间资本。
此外,欧盟于2008年创办全球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基金(GEEREF),撬动的民间资本比例更高。他们的模式是,欧盟政府投入的资金类似种子基金,在股东层面就撬动了好几倍的其他资金,事实上是一个PPP的模式。然后把这个基金作为母基金投入到子基金里面,即以Fund of Fund的形式去投,在创立子基金的过程中,它又撬动了几倍资金。最后他们实现了五十倍的撬动率,就是一块钱原始发起人的资金能够撬动其他政府和民间资金的股权和债务融资达50倍。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追求这么高的撬动率,但用一元政府资金撬动十元左右的民间股权与债权融资还是有可行性的。
绿色金融激励措施 要注重市场化运作
在建立绿色担保机制的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出了一笔钱,但用非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如果不良率超过5%的话,基本上就没法运作下去。
证券时报记者: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过程中,激励政策措施一直是各方关注焦点。您刚才提到再贷款。其实《指导意见》中还包括贴息、担保等其他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具体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较现有的激励政策有何不同?具体落实中,还须突破哪些障碍?
马骏:首先,这里所说的再贷款不是狭义的再贷款。狭义的再贷款是指一年期以下的,央行贷给商业银行的资金,然后由商业银行发放一年期以下的低利息贷款。但其实,可以多种形式通过“广义”的再贷款来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支持绿色金融的“再贷款”,它可以是央行给商业银行利息较低的贷款,也可以是支持商业银行购买绿色债券或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也可以是抵押补充贷款。
贴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机制。以前有一些实践,但总体来说,贴息的范围和力度都比较有限,而且存在管理方面的问题。贴息有3%上限的规定,而且可以享受贴息的项目范围也比较有限。此外,如果没有专业人士进行管理,绿色信贷贴息首先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项目,也未必能控制住风险和不良率。比较好的国际经验是通过绿色银行或者绿色信贷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商业银行来进行贴息。现在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准备这样试点,就是找当地在绿色信贷方面业绩比较好的商业银行,由当地的财政拿出一笔资金来委托它们对绿色信贷进行贴息。跟直接补贴绿色项目相比,贴息也是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来撬动更多的民间资金的有效方式。
担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机制,这个机制在国际上有一些运用。比较典型的有三个案例:一个是美国能源部的案例,用了非常有限的资金撬动了三百亿美元对清洁能源的贷款,不良率控制在2%,远低于预期10%的不良率。还有一个是IFC在中国开展的节能减排项目(CHUEE),为国内170个节能减排项目提供了绿色信贷部分担保。参与担保的机构包括IFC、CDM基金、商业银行等,项目一旦发生违约,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别由各方分担损失。IFC用非常少的钱撬动了很大的一部分贷款资金,不良率控制在1%以下。第三个案例是中美洲经济合作银行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担保的案例。现在国内有些地方都在考虑发起绿色担保的机制,但担保具体怎么做,是放在各地的担保公司内部设立一个绿色担保的部门还是另外新设一个公司,还须进一步探讨。
在建立绿色担保机制的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出了一笔钱,但用非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比如安排快退休、又不懂专业的人去管理,对专业人士又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人才很快流失,最后会搞得不良率很高。如果不良率超过5%的话,基本上就没法运作下去了。
未来或规范 第三方评估质量
未来在认证质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把关。有必要防范一些风险,比如说某些认证机构为了维护跟客户的关系,标准可能比较松懈的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指导意见》中,提出了“研究探索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和评级标准”。据了解,国内现在多家机构都研究制定了本机构的评估或评级标准,未来是否会由官方制定统一标准呢,特别是评级标准?
马骏:第三方评估和评级是两件有关联但又有区别的事情。第三方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对绿色债券支持的项目是否为绿色的认定。到目前为止,虽然监管部门只是鼓励使用第三方评估,绝大多数发债人都获得了第三方评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没有经过第三方评估,市场就不认可的行业现状。
但是未来在认证质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把关。有必要防范一些风险,比如说某些认证机构为了维护跟客户的关系,标准可能比较松懈的风险。但是,由于我国的绿色债券市场还刚刚起步,未来以什么方式规范第三方认证的质量还要探讨,希望业界能够一起参与。
目前的绿色债券评级指的是对绿色债券的环境表现的评估,一般涉及到对发行人或债券的绿色程度的评估(如分为五级),而不是对“绿”与“非绿”的简单贴标。现有的绿色评级的做法是给发债主体环境效益的评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债券评级不同。传统意义上的评级会影响发行成本,因为它跟预期违约率是密切相关的。但目前的绿色债券评级跟违约率还没有密切的关系,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从中长期来讲,绿色评级可以与违约概率建立数量上的关系,但必须要有大量数据样本,需要有几年的发展过程。目前,绿色债券评级标准方面还是百花齐放,穆迪和标普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国内机构中诚信和东方金诚也发布了自己的标准。对评级标准的好坏,我认为,不急于很快做结论,总的原则应该是尊重市场选择。
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 可能会分步走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可能是分步走,但具体有几步,分多久完成,还需要探讨。
证券时报记者:《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了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披制度。特别指出属于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研究制定并严格执行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等内容的信披要求。这是否意味着针对这类企业的强制环境披露为时不远了?
马骏:从这句话的表述可以感觉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可能是分步走,但具体有几步,分多久完成,还需要探讨。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比如香港地区,去年更新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不披露就解释。如果披露成本不太高,企业一般都会披露了,我估计几年内香港就可能过渡到基本覆盖全部上市公司。不过,我们的《指导意见》中事实上已经公布了分步走的第一步,就是把重污染企业先行要求严格执行环境信息披露。
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在于如何帮助这些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进行能力建设的问题。因为很多企业不知道该怎么披露,比如说规定了一些主要指标,包括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等必须披露,企业说我不知道怎么算。这就需要有专业能力的机构对企业进行培训,如果企业自己做不了,就得委托第三方去做,需要有机构去帮助这些企业进行能力建设。
此外,环境信息披露的数字还需要有第三方机构进行解读,变成一般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信息,能够引导投资的走向。我记得最近在宣传绿色信贷的时候,说一年的绿色信贷所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北京的出租车停驶280年,这么一个数字就很形象了,老百姓就听懂了。